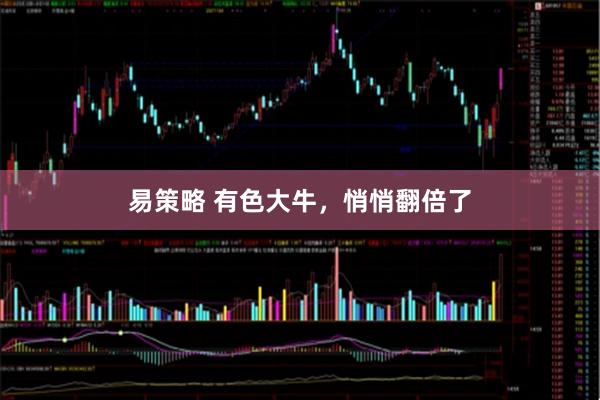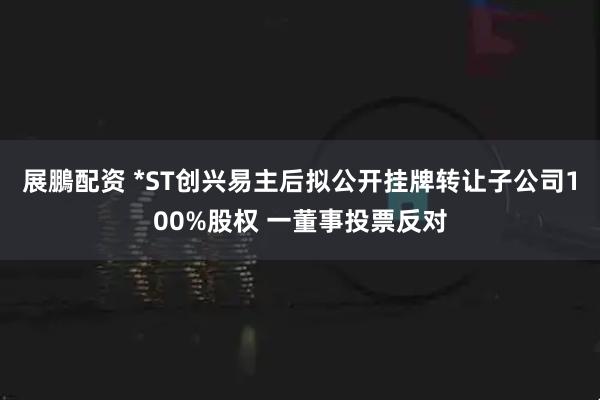在古代社会,为父母守孝是一项无可推卸的道德义务。子女在父母去世后,不仅要在丧礼上痛哭尽哀,还需遵守一系列严苛的生活规范。例如居于简陋的庐舍,饮食清淡,仅食粗粥,不能饮酒食荤,更不能参与宴乐或举行婚嫁之事。同时,孝子们也必须避免夫妻同房,以示哀痛与克己。这些规矩看似细微牛牛配,却被视作孝道的具体体现。然而,问题随之而来:若有人在守制期间行“周公之礼”,该如何看待呢?
在先秦时期,虽然这种事未必触犯律法,但在世人眼中仍属难以启齿的丑闻。那个年代儒家思想尚未独尊,墨家、法家等学派对“守制”并无一致认同。比如墨子就批评儒家所倡导的“守丧不嫁娶、不入内室”,认为这不利于人口繁衍,而人口在战乱频仍的诸侯争霸时代,正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。因而当时社会并未形成严格共识,是否遵守全凭个人选择。不过,华夏自古讲究礼仪,尤其士人阶层更看重行为规范。倘若在哀痛期间仍沉迷床笫之欢,无疑会被人耻笑。《左传》就记载过宋国乐子明与伯父乐大心因丧事互相指责,一个被揭发在丧期行乐击鼓,另一个则被讥讽父丧未满便有子嗣,双方最终都颜面扫地。
展开剩余67%随着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牛牛配,儒家关于守制的规范逐渐上升为国家制度和社会公认的道德标杆。士人们不仅要严守“丧期不入内室”的规定,有些人甚至将之作为谋取虚名的手段。东汉的赵宣就以极端方式在墓旁为父母守丧二十年,声名远扬。但虚伪终难掩盖,他最终被揭露在守制期间竟育有五子,不仅名声扫地,还遭官府治罪为“诳时惑众”。由此可见,社会压力与名教力量已足以将此类行为定性为大逆不道。
然而,人心欲望并不会因礼法而彻底熄灭。许多孝子在表面恪守清规的同时,暗中却偷偷破戒。可惜“纸终包不住火”,尤其当女子腹中孕育新生命时,更难掩人耳目。更为悲惨的是,为了避免丑闻,有的人竟选择溺死在守制期间出生的婴儿,甚至连母亲都遭到抛弃。由于古代医学难以精准判断孕期,一旦孩子的出生时间与守丧期相重合,父亲便可能为自保而无情舍弃亲骨肉。由此,守制的严格规定反而催生了另一种悲剧。
唐宋时期,为了进一步规范此类问题,相关律法被纳入法典。唐律明确规定:若在守制二十七个月内怀孕,则属违法。其判断方式是从孩子出生时间倒推九个月,这虽然并非科学,却至少减少了因“疑似”而丧命的婴儿。然而,两宋在执行时并不算严苛,往往采取从轻处理。比如南宋的赵眘在父丧期间被揭发生子,但最终只是被“解官行服”,远未受到严惩。这既反映出查证困难,也说明皇室乃至士族对延续子嗣的迫切,使律法难以严格贯彻。
至元明之际,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。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废止旧律,守制期间的性事重回伦理约束。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出于人口恢复的考虑,明确否定守制期“不入内室”的规定。从此,明代社会出现了两种极端:一方面,士大夫阶层仍将此视为道德底线,甚至将他人破戒当作打击政敌的手段;另一方面,普通百姓却愈加开放,有人甚至因心学思潮的鼓吹而放纵欲望,毫不掩饰。此时,为了面子与仕途,不少士人宁愿溺毙子嗣,甚至反诬妻妾不贞,悲剧屡屡发生。
到了清代,社会重新回归儒家纲常,虽然律法上未作硬性规定,但舆论压力依然强大。守制期若有子嗣,不仅被视为不孝,更会被认为是祸及国家的“不肖之子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哪怕律令没有明文惩处,社会舆论也足以让涉事者身败名裂。由此可见,关于守制的伦常规范,几经曲折,始终在约束与人性欲望之间摇摆。
(全文约1200字)
发布于:天津市第二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智赢策略 “绩差股”美股盘前下行
- 下一篇:泸深在线 伺服电机带刹车片的作用是什么?